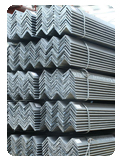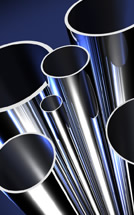小的時候,最羨慕同伴的家里有一輛摩托車,每次看見鄰家父親騎著摩托車風馳電掣而至,轟隆聲如春雷滾過,留下一道青煙,也把一道羨慕的烙印深深刻在我心上。那時,摩托車實屬稀罕物件,唯有家境殷實者才可擁有。我眼巴巴望著小伙伴絕塵而去,只能把羨慕和那未散的青煙一同吸進肺腑,又默默咽下。
初二那年,父親終于也添置了一輛摩托車。那天晚上,家中擺了兩桌酒席,父親的好友們高聲祝賀他喜提愛車。門外鞭炮噼里啪啦炸響,漫天紙屑如蝶紛飛,我悄悄走近那嶄新的藍色豪爵摩托,伸手撫摸冰涼的車身,低低祝福道:“爸爸出入平安。”那聲音被鞭炮聲吞沒了,卻在我心里種下了一顆沉甸甸的種子。
自此,父親便與這個伙伴形影不離。他騎著它奔赴一個又一個工地,無論晴雨寒暑。那摩托車上,總斜斜綁著他那起了毛邊的工具包,裝著那把油亮厚實的磚刀,刀柄處磨出深深凹陷,如同父親手掌上厚厚的老繭一般,都是光陰咬下的印記。它載著父親在風里雨里奔波,也載回了全家人的生計和希望。
每遇逢年過節(jié),走親訪友,我便最愛攀上父親摩托車的后座。車一發(fā)動,風便迎面撲來,路邊的樹影與田野急速向后退去,我貼著父親寬闊的后背,仿佛貼住了一座安穩(wěn)的山巒。車子疾馳,風聲在耳邊呼嘯,我心中竟也似生出翅膀,自由地飛起來,卻又被父親后背的溫暖穩(wěn)穩(wěn)托住——風越急,父親后背的溫暖反而越清晰。
后來,我升入高中,父親謀生的足跡也漸漸伸向更遠的異鄉(xiāng)。摩托車后座上的日子,便如沙漏中的沙,無可挽回地滑落、減少、終于消失。我負笈遠行,奔赴他鄉(xiāng)的學堂,父親則暫別那匹日漸老邁的鐵馬,奔向謀生的遠方。
再后來,我便如蒲公英的種子般飄落異鄉(xiāng),開始獨自謀生。時間像無情的潮水,沖刷掉許多東西,也沖淡了歸家的次數(shù)。
這一次離家時,我特意選了最晚一班火車,父親執(zhí)意要用摩托車送我去車站。于是,相隔多年,我又一次跨上了那熟悉的后座。
父親今日騎得極緩、極小心。昏黃路燈的光暈流淌在他身上,我凝視著他微駝的背影——那曾經(jīng)寬厚如山的脊梁,仿佛已被歲月削薄。頭頂逐漸稀疏的頭發(fā)和脖頸間深深的溝壑仿佛訴說著他已不再年輕。父親沉默地握著車把,載我前行。那些呼嘯在風里的年少時光,仿佛已被緩慢的車速遠遠甩開,在身后模糊成一片迷離的煙塵。
摩托車終于停在火車站前。我緩緩下車,父親摘下頭盔,那張被歲月反復雕琢的臉孔在燈光下完全顯現(xiàn),溝壑縱橫。他什么也沒說,只是對我點點頭,揮手示意我快些進站。我轉(zhuǎn)身進站,再回望時,父親依舊跨在那舊車上,身影在空曠的站前廣場上,竟渺小如一粒微塵,又固執(zhí)地凝固成一座沉默的山丘。他停駐原地,執(zhí)著地目送我的背影,如同當年我在街角目送他摩托車的尾燈消失于黑暗深處那般——人生兩端的凝望,中間竟橫亙了如此洶涌無情的歲月之河!
車站的電動扶梯無聲地載我上升,父親的身影終于被緩緩淹沒。在機械的上升中,耳畔似乎又響起了那輛舊摩托引擎的轟鳴——那聲音從記憶深處傳來,曾經(jīng)載著父親奔向生活的戰(zhàn)場,也曾載著我奔向未知的遠方。它負載過我們兩代人的道路與重量,卻終究載不動那疾馳如箭的時光,更載不回父親在鞭炮碎屑中熠熠生輝的青春容顏。
時光的摩托車,終究是單程的奔赴;父親的后座,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原鄉(xiāng)。我多想坐上那后座,回到那年鞭炮炸響的夜晚,對著嶄新的車身,再說一遍那被淹沒的祈愿:父親,我多愿您再年輕一回!(漢鋼公司 胥京)